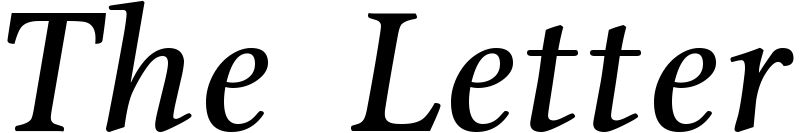我在大學第一次接觸到美國的黑人文化,也因此,我成為了更好的人。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距離Cabrini Green不到一個街區。我教Pierre怎麼游泳,他則教會了我如何原諒。我的室友Ronnie,曾是非洲人覺醒學生組織的主席。他花了三年試圖告訴我,問題是在系統之中的,「是系統,Jesse。它隱蔵在系統之中,我知道你並未察覺,但它充斥在我每天的生活中。」,我聆聽著,但我依然無法看到他口中的問題。
而在台灣生活了十年,打開了我的眼界。Ronnie,我看到它了。我終於不單單只是聽到它,我終於用我自己的眼睛看到它了。我也看到了,其他人沒看到,尤其是當他們身在其中。
如果有個人認為他不正義的舉動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就沒有任何方法在他這樣想的情況下告訴他他的所作所為是不正義的。藉此,我知道Rosa Parks感受如何。我完全贊同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所提到的:
「到處都是不正義之事,不論在哪都對正義是種威脅。」
「我們再也承受不起與狹隘的、偏狹的『外部煽動』的主意共處了。」
「我們可以很簡單地同意,當時機到來時我們達到我們的期望。我在這裡是因為我被邀請至此。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不正義在此。」
台灣人們需要西方人。他們在他們的機場和市場歡迎西方人。但他們需要的是西式的訓練和西方的思考方式,工程師為了抵抗區域內強大的侵略者而建造屬於他們的防衛性武器。台灣需要英文老師;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需要每天和英語母語者交流。然而,因為對岸那個巨大的威脅,以及過去被殖民的傷痛,台灣制定法律限制所有的外國人。台灣因為過去,而拒絕他們未來需要的朋友。我們都做過一樣的事情,對吧?
我接下來要說些很無聊的細節,請大家忍受一下了。在美國,工作簽證能夠給你居留權,五年之後外國人可以成為公民。相較於美國,台灣比較複雜,台灣在這方面有著許多奇怪的限制,例如:你如果在星期一被解雇,而你在禮拜三才找到新工作,你的五年就要重算;而且如果你被開單,五年也要重算;且證明這五年是有效的,需要多次的工作允許證來證明,但政府不直接給我,而是給我的老闆,而我的老闆從來沒有給過我。即便你上述條件都符合,你要成為公民還需要放棄你原先的國籍。
我的故事從12年前開始,我的老闆不給我我的工作許可,然而法律上只有要求但並非強迫他要給我,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工作許可偷來,並藏在我的領帶裡,然後回家爆哭一頓。我遇到的下一個老闆,他依然不給我工作許可。因此我向警察和移民署求助,那個接我電話的警察大喊:「他們必須要給你」,然而他們就沒有後續的處理了。
很快的,在地的勞工督察找上了我,但是是在我不該出現的補習班找到了我,我當時在一間連鎖補習班工作,但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該在哪裡上班,我工作地址是用中文寫在那我從來沒收到過的工作許可上的,接著我收到了督察的傳喚,我的老闆超級擔心,叫我對政府單位說謊,我們甚至為了我要怎麼說謊開了一個會,老闆的老闆用奇怪方式和我握手,我感覺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脅。我的公司的所作所為就是為了欺騙政府好躲過審查,當時我和我老闆坐在一起,對著勞工局的督察(一個人很好且在乎你,但沒什麼權力的人)撒謊,而我老闆的老闆則是進入了他們長官的辦公室,偽善的和他聊天著。那個長官看起來嚇壞了。最後,我為了那出於被威脅而說的謊言押上了我的指紋,我們就像什麼都沒發生的樣子離開了。
幾個禮拜後,我才知道原來那個詭異的握手是性暗示,我這才知道自己被性騷擾了,並且如果我不聽他們的向政府說謊和同意那個性要求,他們打算找他們的黑道朋友找我麻煩,而我拒絕了那個要求,或許這就是幾個月後公司想把我炒了的原因,且開除員工需要給付資遣費,而他們一向拒絕給付。
在合約結束前兩周,老闆基於我自願性的回報工作進度,他們突然說要進行一場考核,就為了找出為什麼我的教學進度落後一頁,而且他們表示絕對不會跟我續約。荒謬的是,正常情況下任何老師的教學進度都差不多落後表定三頁左右。
法律上,老闆應該要接受我的辭職,但他拒絕了。為此我去了兩趟警察局,但警察卻從不強迫老闆送出相關信件。接著,老闆舉報我無故缺席(這對外國勞工是違法的),然而聰明如我,我早就向勞工局提出我想要辭職的渴望,我給了那個勞工局的督察(上面提到的那個,人很好且在乎你,但沒什麼權力的人)寄了一封信件,裡面內容包含了我承認自己當時做了偽證以及證據,我還附上了一張CD裡面有著我老闆說:「我恨外國人的」的錄音。那個督察收到我的信件後,安排了一場調解會議,然後打電話通知我一定要帶上台灣朋友翻譯。
這場會議持續了三個小時,而結果以老闆接受我辭職收場。這是個突破,過往雇主和外籍勞工的爭執,往往都沒有達成協議,然後告上法庭或是勞工被驅逐出境,而我是台南的第一個成功的先例。
我問了那個陪我去調解的朋友,為什麼我的老闆一開始要在我的工作地點上說謊,我想不到任何理由要在一個事實並不傷害人的的情況下說謊。他回答:「因為文化大革命。老一輩的人受到了毛主席很大的影響,包含像他這樣說謊。」,他也告訴我那個大老闆控制了當地的「英文教學界的黑幫」之類的東西。
不久後我前公司的同事跟我說,那個人很好的督察在看到我的情形後,決定繼續觀察那間公司,然後那個補習班倒了三間,那間補習班突然間對我的那位前同事很好、很尊重他,他們過去也曾試著要開除他,我很開心她的處境有了好轉。
不久後,我之前的直屬上司因為他們之前對我做過的糟糕事也辭職了。她改行去拿更多薪水而且還更少壓力的工廠工作。我也很為她高興。
然而,我的下一個工作的老闆告訴我,因為我的前老闆一直騷擾牠們,所以他們必須要辭退我。現在回頭看,我不知道我怎麼度過那段艱困的歲月的。我想是神的指引吧。
移民局的員工、市政府的工作人員、和兩個立委助理都問我:「為什麼我不搬去台北,那裏有更多工作機會,而且這樣你的前老闆也沒辦法找你麻煩。」
每當遇到有人欺凌,他們往往選擇屈服。這是過去蔣介石時代所留下的遺毒,正如以色列人因為受過埃及人的統治,就害怕前往他們的應許之地。這正是台灣人的困境!所以針對上述的問題,我的答案是慈祥的、有力的且令人安心的「絕不!」,可沒有任何一條法律禁止美國人在台南教英文,也因此政府應該要保護一個願意跟台南人民共處的美國人!而且台南人們的英文跟台北比起來也需要更加進步。台灣的政府依然不打算幫助我,而我甘願受苦是因為我愛台南。
而唯一給我幫助的,是一個了解問題所在但從來沒直接跟我說話的人—那個勞工局的督察(上面提到的那個,人很好且在乎你,但沒什麼權力的人)。
那些用著孩子般天真的態度問我為什麼不搬到台北去的人們,他們並不知道他們這樣的言論不單單只是歧視我而已,同時也歧視了台南人們。許多西方人住在人口繁雜的北部,但在台南有著許多令人喜悅的事。台灣人以訛傳訛的以為因為它是個大城市,因此西方人較喜歡台北。但實際上,是因為勞動部對南部的小型的英文補習班和北部的有錢英文補習班有一樣的要求,造成了他們沉重的財政負擔,進而造成台南的補習班並沒有足夠的經費去合法的雇用美國人,所以他們需要從黑市找人,而傳聞我的前老闆控制了那個黑市貿易。儘管因為台北的法規,台南和台北不太可能有黑市方面的連結,但我看到更重要的是:
西方人避免來到台南因為當地的英文補習班市場被不可見的黑市控制了,而這不只傷害到我,也傷害了選擇保持無知的台灣人。
而我也因此知道,當非常接近問題的人選擇不正視問題,系統將會壓迫人們。事實上,台灣人並不知道勞動法規是怎麼殘害台南的英文教學。台灣人和我一樣都是系統性偏見的受害者,我上述的複雜情況(那些不合理的要求…),都在殘害著台灣人渴望的英文能力。但如果台灣對美國人就像美國人對台灣一樣:維護他們的權益和保護他們,問題將不復存在。倘若如此,許多美國人取得雙重國籍將可以讓他們有資格在任何地方工作(包含較沒經費的南部英文補習班等等….)。
然而儘管經歷了11年的請願,台灣政府依然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並且,當因為台灣的邦交國紛紛跟台灣斷交,台灣在請求幫助時,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對待移民的法律也是造成他們如今處境的一部分原因。
故事最精采的部分來了,我之前工作的那個英文補習班接受了美國政府的公共資金。我打給了他們的美國辦公室去通報這件事,但他們直接一聲不吭的把我的電話掛斷。而我不會透露消息來源,因為消息取得的方式是違法的,我想幫台灣人民,幫助他們抵抗那些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不誠實的企業。12年過去了,時日至今,我依然期盼一個對當年事件的回覆。
七年以來,我每個禮拜一都會寫一篇以客觀角度並且尊重台灣有事實主權的方式的社論,但我承認我有時候會偏袒台灣。2014年時,我稱讚台灣警察並沒有對闖入立法院的學生使用暴力,因為我在台灣我才了解,這跟華盛頓的警察形成了對比,那些闖入美國行政部門的學生就沒台灣的學生那麼幸運了。蔡英文總統曾說:「台灣是個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我們有許多問題,但都值得去解決。」,她借用了我寫給美國國會的信中的字。
在過去的12年,我從來沒有沒有公開過我的控告者的名字,也沒有發布可以從中知道我在何處的文章,我這麼做為的就是和平。我知道台灣需要時間去改變,但至今我依然沒看到改變,工作許可依然由老闆把持著,取得雙重國籍的權力依舊不存在。
我曾經兩次向政府申請永久居留權。第一次,委員會對此的投票結果是否定的,我可以證明那一次的會議是失序的,因為政府為了否決我而毫不掩飾把數分鐘的的會議寄給我。我以對媒體業的貢獻,並且向他們表達我未平息的冤屈以及我的耐心,還有最重要的—沉默,向他們第二次申請。對我的申請的回覆應該是90天,而移民署超過兩百天都並沒有對於委員會的投票給我一個正式的回覆。
我唯一的結論是愛,我無法因為這系統性的問題而恨台灣。黑人並不會因為我系統性的歧視而恨我,我並不知道我對他們做了什麼—因為我身在這系統之中因此我無法了解和看到它,我們不應該為我們自己找藉口,但黑人並非為了什麼目的而小題大作。我培養我成白人共和黨人,我必須學著去聆聽黑人就如同我知道台灣人如果想了解我是必要聆聽我所說的話。
這個訊息曾是我渴望讓美國人知道的:我們系統內看不到的不公義導致了貧窮!但我想,我如果這樣做將會傷害到台灣人,而現在,經歷了等待那期限應該是90天的回覆兩百多天後,我想移民署並不會在乎。
當然,我有很多我認為真的很好的台灣朋友,許多都是滑板人。為什麼我會選擇台南,一個在台灣滑板受到最多限制的城市(滑板場和法律)?台南有充滿天賦的滑手,就跟其他地方的滑手依樣有著好勝心跟天分。在任何系統中的不公義會影響每一個部分。面對問題,我從不逃避,不論是大是小。要離開朋友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尤其是他們用他們的耐心改變了我的人生,過去12年台灣打開了我的眼界,讓我了解了黑人艱難的處境,它讓我更了解我的家鄉,因為它不斷拒絕我得請求,並且我一直試著和他們溝通。
我無法拒絕台灣人,他們教我太多了。 · · · →